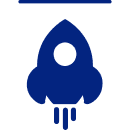凸显科技创新突破
逐步构建成熟体系
因进口受限被迫进行自主研制,经过卧薪尝胆终于进入世界前列,这就是中国在挖泥船领域的科技创新故事。类似的故事也在其它领域不断发生,它们一起形成了蔚为大观的中国科技创新集群,支撑综合国力逐渐提升。为了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形势,维护国家安全、保持竞争优势,同时也为反制一些国家对华歧视性出口管制,中国逐步形成了一套出口管制体系。中国计量大学副教授姜辉表示,自1984年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始,中国在重要领域对关键技术和产品实施必要的出口管制并形成了一套体系。
对我国出口管制的整体发展历程,姜辉介绍说,改革开放初期的出口管制重心局限于“防扩散”,管制对象包括核、生物和化学武器等物项。到20世纪末,许多战略性资源被纳入出口管制清单。新世纪以来,中国高新产业的技术创新不断取得突破,可供管制和需要管制的高技术物项也越来越多。这推动我国出口管制战略目标由一元转向多元,出口管制体系逐步走向成熟。
刚公布的“最新《目录》”是对商务部、科技部令2008年第12号公布的《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修订后)调整后形成的,而该目录修订前文本由当时的外经贸部与科技部于2001年12月发布。对未来方向,商务部服务贸易司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表示,商务部、科技部仍在有序推进目录修订工作,将对其进一步删减调整。
姜辉指出,仔细研究上述调整内容,不难发现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出口管制的特点,即物项正逐步呈现多样化趋势。而从我国出口管制物项的整体演进来看,威胁人类共同安全的生物、化学和核等物项必然长期列入出口管制清单,而影响国家技术领先优势和战略利益高性能计算机、无人机、战略资源及其他军民两用物项等则根据时局的变迁而适时地列入出口管制清单。这既是中国从技术追赶到技术超越的必然结果,也是为维护国家安全、保护本国环境、维护竞争优势等做出理性选择。
姜辉的阐释可以从“最新《目录》”中深刻体现出来。比如,“最新《目录》”将“卫星应用技术”控制要点1表述为“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替代之前的“双星导航定位系统”,反映了从北斗一号到北斗三号的技术飞跃。再比如,“最新《目录》”在信息处理技术项下大幅增加5项控制要点,其中包括广受关注的“基于数据分析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技术”和“人工智能交互界面技术”,折射出中国近年来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的创新突破。
处理好辩证关系
推进法治化进程
无论是对挖泥船以采取公告的形式予以临时出口管制,还是通过调整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实施的系统性出口管制,都是有关部门依法实施行政行为,所援引的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等,出口管制的具体内容都是在征求相关部门、行业协会、业界学界和社会公众意见基础上拟定的,充分考虑相关措施可能带来的影响。
姜辉指出,我国出口管制的法律基础包括国家对外贸易法、海关法和刑法等,而出口管制的专门法律体系则由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相关文件组成。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国家出口管制法草案发布,标志着我国出口管制开始由行政部门规章监管迈向国家层面专门立法监管。今年7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草案二次审议稿)》进行了审议,随后向公众征求意见。可以预期,该法将很快完成立法程序并出台实施,为维护国家安全和保持竞争优势提供更完备的法律保障。
构建适合本国国情的出口管制体系根本在于一国科技创新能力。姜辉强调,大力推进创新,成功实现技术追赶是中国出口管制体系构建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掌握国际前沿技术,也就失去出口管制的必要。从实践上来看,被纳入的出口管制物项大多涉及“ 载人航天 ”“无人机 ”“ 挖泥船 ”“高铁”“北斗导航”,而这些都是我国实现重大科技创新突破的领域。可以说,“最新《目录》”就是中国科技创新的“争气目录”,最新版就是中国打造的技术“争气目录”升级版。
在姜辉看来,处理好加强高新技术出口管制与促进对外开放的辩证关系是中国的重要经验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我国出口管制体系建设不断取得成绩的同时,始终秉承开放贸易原则,推动包括技术出口在内的国际贸易稳步快速发展,实现了向贸易大国的转型。据统计,中国技术出口合同金额从2013年的200亿美元提高到2019年的321亿美元。货物进出口贸易规模由1978年的约206亿美元快速增长至2019年的约4.6万亿美元。
链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20-09/07/content_2007605.htm